|
这几年,关于“极端通勤”的新闻越来越多,“全国仍有超1400万人口承受极端通勤”、“全国超800万打工人每日通勤上百里”。 带着对这些数字的惊诧与好奇,我们对极端通勤进行了探究。通常语境下,单程通勤时间高于1小时的,被定义为极端通勤。我们访谈到的“最极端”的通勤者,每天有近6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在拥挤而憋闷的车厢中,通勤者们深感消耗,也焦躁于被剥夺的时间、被侵犯的边界。 极端通勤是大都市圈的标配,是全世界与全人类的难题。而完美应对的样本还没有出现。可以想见,为了让上班的路更幸福一些,人类或许还有许多别的路要走。 “我就是一块肉” 中国陆地边界长度大约2.2万千米,如果忽略海拔的变化,要在一年内环中国一圈,每天需走60公里。 魏巍住在河北省廊坊市燕郊,供职的公司在北京市西城区积水潭。一年的248个工作日里,他每天通勤往返92公里。只用这248天,他就可以环中国一圈。 他早上7点出门,7点半,在燕郊意华小区站坐上815路公交车。8点45分左右,他随车到朝阳大望路,下地铁,1号线转2号线。9点半,出西城积水潭地铁站,再步行一小段距离,9点40左右到达公司。 从走出家门,到进入办公室,他平均用时超过两个半小时。晚上返程,因为排队和拥堵的延长,这个时间会增加到3小时。每个工作日,他花费至少5个半小时在路上,一年就是1364小时,约等于57天。 这一路没有舒适感可言。从他上车的那站起,815路已显得拥挤,往后的每一站,陆续上来的人会把剩下的每一道缝隙填满。 为了有一个座位,他有时会提前半小时在公交站台排队,冬天受冻,夏天暴晒。但与他共同等待的人还有很多,队伍甚至会拐进站台后的停车场里。努力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里获得一个座位,意味着身体的舒展面积能多0.2平方米。 最不适是在1号线大望路地铁站,“下地铁站的楼梯很长,往下走,有一种下地狱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你马上要面对什么。”2024年,1号线的日均客运量是88.06万人次,排名北京第三。前几年,他通常要等三班地铁开过,“才能被后面的人硬推进车厢。”这两年好些了,一到两次就能挤上去。 “哲学意义上我就是一块肉,从这里被运到那里上班。下班后,又从那里被运回这里。”魏巍说,“我有什么感觉?我没有感觉。每天跟将近一百万的人在同一条线上挤来挤去,什么人都会变得麻木。” 将目光从哲学转移到城市规划学,魏巍正经历着“极端通勤”:在美国,这个词汇指向50至100英里(80.47公里至160.93公里)的通勤距离;在欧洲,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00分钟是极端通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则将单程60分钟以上的通勤,定义为极端通勤。 根据该研究院在2021年、2022年的数据,中国44个城市中有超过1400万人承受着极端通勤;2023年,超大、特大城市中有800万人的单程通勤超25公里,耗时90分钟以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都是极端通勤的高发城市。其中,北京以30%左右的极端通勤人群比,常年位居榜首。换句话说,在北京,每3到4个上班族中,就有一个人的单程通勤时间超过一小时。 通勤距离越长,留给自己的容错时间越短,这是受访通勤者们的共同经验。人们计算出效率最高的通勤线路,好多睡一会儿、晚出门一会儿。而只要其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错,整段行程就会失控。 亚梦是往返于北京大兴与望京的通勤者,早上经常从家拼车到最近的地铁站,这正常耗时10分钟左右。有一次,她拼到一辆“绕特别远、等其他乘客特别久”的车,10分钟被拉长到了30分钟,致使她最终迟到。疫情时的一天,魏巍6点多就出门等公交车,但被堵在燕郊的进京检查站外近3个小时,中午11点多才到公司。 小闫是极端通勤中的极端案例,他家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每天搭乘网约车、高铁、地铁和公交,到北京朝阳平乐园上班,往返超过250公里。中国的陆地边界线已经接不住他的通勤距离了——赤道长度略大于4万公里,上下班一年,小闫可以绕赤道1.5圈。 有一天下班路上,只是下了一场雨,“路上堵了那么一下”。公交车陷入车流,他也陷入纠结:是继续等待,还是下车,直接搭地铁去高铁站?按他日常的通勤方案,容错时间只有几分钟。一旦错过那班回怀来的高铁,临时改签怕没有车次,那么今夜在北京他将无家可归。 最后,他还是下了公交,回头狂奔,在平乐园地铁站坐上4号线,又换乘15号线、昌平线。高铁停止检票前一分钟,他冲到了检票口。那是他此生最激烈的一次冲刺,坐上高铁,还觉得气血上涌,几欲晕倒。 拥堵、误车、天气变化……在这些强烈的不确定性中,如何寻求哪怕最轻微的可控?通勤者们逐渐领悟出技巧。 比如,6点下班,最好不要立刻去搭地铁,等15分钟再走,同路竞争的人会少一些;只要能穿过等待的人群,就尽量往地铁的首尾车厢走,那里相对空,人与人的间距可以增加到十几厘米;特定的车站会多下人,在快要到达那些车站前,挤到坐席边等候补缺。不确定哪一站下的人多时,就观察有座乘客的神情和肢体动作,下车前,他们会忍不住抬头看线路图——同样的,快速凑到他们面前准备“补位”。可以买个折叠小马扎放在背包里,没座位的时候就打开坐会儿。尽管许多时候,车厢里并没有能撑开小马扎的空间。 如果实在无座可求,站立也有黄金位置:在公交车上,后门边有个台阶可以坐下。在地铁上,是竖立的扶手杆周围,这杆子可撑、拉、靠,用途灵活。不管是在公交车还是地铁上,贴着墙壁,都比贴着人舒服。 许多个晚上,在大望路坐上回燕郊的公交车前,魏巍会顺路去SKP解手,这是一位通勤打工人的“奢侈”。那里的马桶是智能的,厕纸、一次性坐垫、洗手液和护手霜一应俱全,环境干净,人又少。这是体恤身体,也是慰藉内心。毕竟,在之后的一到两个小时里,他没有地方方便,更无法逃脱拥挤。  图源剧集《值得爱》 “租过的都不满意,满意的都租不起” 关于通勤,人类有过美好的想象。 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曾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希望城市节制发展,扩张至一定规模后,转而发展附近的新城,使每座城内的就业和居住平衡分布,居民的工作“就在住宅的步行距离之内”。 一百多年后的21世纪,这个愿景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都市圈中都已落空。 去年的两则新闻提到,有6.4万名“超级通勤者”从纽约三州以外的地区,跨市赶赴曼哈顿工作;东京上班族的每日平均往返通勤时间是95分钟,全球最长。 究竟为何会出现极端通勤?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大城市病”,是城市化的附带结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政策、地价的原因,北京的房地产建设不断向郊区推进。在今天看,北京及周边著名的“睡城”都在五环外:天通苑、回龙观各常住约30万人,燕郊常住约60万人。 就业机会的发展则是另一套逻辑。北京的就业区域富有个性,又彼此独立。人们在穿梭的地铁上就能总结其规律:14号线近望京时,背小包的白领多;4号线经北京南站前后时,拎着蛇皮袋的体力劳动者多;接近中关村时,就格子衫、冲锋衣多。国贸附近最精致,很多女孩一边出地铁一边化妆……这些区域间至少相隔十余公里,与“睡城”们更是动辄二十公里以上的距离。 2019年,武汉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科研机构发文指出,北京居民主要的就业机会大多在四环内的中心城区。同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北京市一半以上的常住人口居住在五环以外。 在大都市里,“住得远”,常常是多方妥协的结果。 依魏巍的预算,租房成本不能高于月收入的30%,在这范围内越低越好。但他也是个对居住品质有要求的人,搬到燕郊前,他租住过十里河、传媒大学和通州北苑等区域,“一环一环搬出去,越搬越远。”就是试图在价格与居住品质间寻求平衡。直到他慢慢发现,这种平衡在北京市内难以获得,“北京的房子就是,租过的都不满意,满意的都租不起。” 他在通州北苑月付3200元租过一个小一居,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造的,装修风格则是90年代的。家具老旧而潦草,淋浴喷头锈得喷不出水来。他当时在一个很体面的单位上班,出差总住设施高级的五星级酒店。回家因此更让人痛苦,“你就发现你的生活是很割裂的,外头的光鲜亮丽都是虚的,回到出租屋,才回到现实。” 后来他搬去了燕郊,这样的割裂不复存在。他和太太月付1300元租了一个70平方米的大一居,朝向、格局、装修都好,家电家具又新又干净。马上,他们预备每个月加500块,搬到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去——在北京四环内,同样条件的房子,月租不会少于八九千块。 这些年,他换了几份工作,收入变得不稳定,是燕郊的低房租让他得以喘息,“就算三四个礼拜接不到活,压力也不会太大。”他懂得的,在大都市圈,要么花钱买距离,要么省钱花时间,两者总要择一。 小闫是坚定选择后者的那类人,也是最资深的极端通勤者。北漂近10年,除了刚开始短暂地住过公司旁边,“上班只要走10分钟。”往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租住在房山,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左右进城上班。他算过,每年能省出至少两三万的租金。 去年年底,他干脆搬回了老家怀来——老家的房子是自己的,再也不用付租金了,还能陪着太太。要知道,太太一直在老家工作,他们结婚5年,有4年多都是异地分居的状态。他们渴望互相陪伴,即使代价是,他的通勤时间从单程1.5小时增加到了2.5小时。或许是因为常年的长距离通勤锻炼出了他的忍耐力?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幸运,反正他几乎已经忘记步行就能到公司的滋味。 在朝阳门上班、昌平居住的Bill曾经很不一样。来北京8年,他换了4份工作,搬了6次家,前5次都是家随着工作迁徙。多数时候,他把通勤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 最后一次搬家前,他在西二旗上班,女朋友在大钟寺工作,两人折中距离、公司补贴范围,在清河地铁站附近租了一个半地下室的loft,月付5000多块钱。住了两年多,因为地下潮湿,他的鼻炎反复发作。 他开始感到疲惫,想要停止流动,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好一些的环境。他决定买房,但手头的预算有限,“五环内基本不用考虑。”五环外看了一圈,他最终在昌平老县城买下一套商住两用小户型。他的通勤距离飙升到每天往返八九十公里。 做买房的决策时,通勤距离当然曾纳入考量。但没有办法,“你就只有这么一笔钱,只能买这个范围外的房子。” 他想了两种思路来安慰自己: 看房时,他被昌平街上“慢悠悠溜达、慢悠悠说话的大爷大妈们”吸引,他们不像中心城区的人们那样行色匆匆,有一种“不在北京”的松弛感。为了沉浸在这松弛里,他愿意忍耐长距离通勤,“工作会换,但居住是长期的事情,要选择自己内心更向往的环境。” 而且,以前他租住在公司附近时,通勤太便利了,反而容易在办公室久留,不知不觉“自愿加班”。社交圈子里也都是就近居住的同事们。生活与工作缠在一起,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看到过一个理论,要组织一场成功的团建,最好选择距公司5公里以外的地点。“你只有逃脱了公司的环境,才能真正做到放松。”他希望居住也是同理。  图源剧集《我的解放日志》 被剥夺的与被侵犯的 实际当然事与愿违。一旦聊起极端通勤,“郁闷”才是最常被提起的词汇。 几乎每个受访的极端通勤者都提到,最郁闷的是早上闹铃响的那一刻,“不想起床”、“每天都想把工作辞了”。有时,郁闷在前一夜设置闹铃时就到来,让人焦虑得难以入睡。 睡眠被转移到了通勤的车厢里,在早晚高峰构成一幅疲惫又匆忙的场景:歪着、坐着、蹲着、站着,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睡姿。会睡着,但很少坐过站——所有人都坚称,那是一种临界状态的睡眠,是半睡半醒,所有人都能在到站的一瞬间睁开眼睛,“一种肌肉记忆”。《通勤梦魇》一书里有过类似的描述,“列车的节奏早已蚀刻在城市居民的身体里。” 如果不睡觉,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机了。早晚高峰的通勤车厢里像有成片的密林,躯干间密不透风,但总有举手机的臂膀从斜里伸出。有人来北京前,就听说过这里的奇观:“甭管地铁、公交车有多挤,大家一定有办法把手机掏出来玩。”小闫也很快掌握了这个技能,这有时需要一点柔韧和耐力。 关键是,不睡觉、不玩手机,通勤者们还能怎么打发时间呢? 有人在通勤路上重温了《海贼王》和《雍正王朝》,幸好只是重温——地铁上,每15、20分钟就要上下换乘,人是无法长时间静止的,观剧的体验很差。有人站着时从不听音乐,也很少看书,“怕被吸引注意力,不能及时发现有座位空出来。”只好玩《羊了个羊》这类机械化的游戏。 漫长的旅途积蓄着坏情绪,一些爆发时刻让人印象深刻。 有一次早上坐公交,Bill见到一个女生被夹在前门外的人群里,她大声哭喊着求大家让她上去,否则,她就要迟到了。但大家都无能为力。好几个乘客的臀部都已经露在车外了,司机硬关上的门。 小闫在地铁上常能旁观吵架。可能只是碰了一下肩膀,两位男士就互相推搡起来,一个把另一个的眼镜打掉了,最后叫来了警察。“我想,就这点小事,上班忙一天了,何必呢?但又想想,上了一天班,谁的怨气不大?” 有多篇论文表明,极端通勤会对人的生理、心理造成损害,导致睡眠紊乱、肥胖、更多的肌肉骨骼疼痛和胃肠道问题,甚至患抑郁症的风险也在增加。 西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林超越访谈了全国各地的30位极端通勤者。有人告诉他,因为地铁上的风声、人声太嘈杂,他长期在车厢里戴着降噪耳机刷视频,这两年明显感觉到了听力下降。“工作附加时间延长”、“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每天都很忙碌,但是除了工作以外,其他鲜有收获”……也都是林超越常常听到的抱怨。 和Bill最初设想的一样,昌平环境好、节奏慢,是宜居的。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心情,昌平的松弛、拥有自住房的喜悦只让他开心了一阵子。开始体验极端通勤后,他很快低落下来。 更年轻一些时,他在互联网大厂上班,同事们年龄相仿,住得也近,节假日经常约着出门玩耍。现在在昌平居住,这类社交就变得很少了。节假日,他非必要不进城,因为“进城的路线和上班的路线基本上有90%的相同”,去玩也像是去上班,兴致全无。 亚梦与Bill相似,已和爱人在大兴买了房。原本她在媒体行业工作,不坐班,没有任何通勤的困扰。她也没料到,搬进新家不到半年,自己转了行,开始每天到望京上班,往返加起来3个小时。 这3小时像是忽然从她的生命中被剥夺了,她与它共度,却并不掌握它。这3小时本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散步、逛街、收拾家里卫生、和爱人聊聊天……去年刚搬进新家时,她在附近的游泳馆办了一张卡,到今天只游了20次。她每天7点下班,8点30左右到家,还要收拾泳衣,骑车到游泳馆——游泳馆9点闭馆,再怎么掐点也游不上。 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就总是报复性熬夜到1点多才睡。她其实需要睡的觉很长,所以每天早上都头昏脑胀。她又认床,在通勤的公交、地铁上也睡不好,只能在周末补觉,一口气睡到下午1点,“工作日活人微死,双休日死人微活。” 还有更糟糕的通勤体验,源自被侵犯的边界。 那天在地铁14号线上,亚梦发现对过有个中年男子盯着她看。她瞪他,他也不移开目光。她走到另一节车厢,他跟了过来。地铁靠站时,她立刻冲下车,跨过两节车厢又上了车。“我想他总该以为我走了吧。”但隐约之间,她好像又看到他朝这里走来。 几分钟后到了换乘站,她惊慌地下车,一路小跑,几次擦到路人,都觉得害怕。 当时是夏天,她刚开始极端通勤不久,没有任何防备的经验。她穿了一件勉强算紧身的针织衫,下身是到小腿的绸缎裙——她通常的态度是绝对的穿衣自由,但这次以后,她还遭遇过两三次类似的目光侵犯,她逐渐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狭小的车厢空间、高密度的人群、长距离的出行,不安感是那么强烈,她不得不考虑,以后要披件防晒外套。  图源剧集《北上》 锚点 2020年的一次TED演讲中,法裔哥伦比亚城市学家卡洛斯·莫雷诺讲述了“15分钟城市”的概念:城市应该被重新设计,以便市民们通过15分钟内的步行或骑行,满足对工作、住房、用餐、医疗、教育、文化和休闲等多方面需求。这与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有相似之处,但更细致,莫雷诺将城市中心设想为生活、社交和工作三区共存的模式。 在另一场访谈中,他也曾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把很多人赶到房价更低的郊区,告诉他们,‘坐火车,你就可以花一小时上班和下班。你要为有一份工作而感激,因为世界属于早起的人’……我们不能再在更远的地方建设城市,建造起三、四个新的火车站,然后对人们说,来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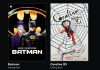




Copyright © 1999 - 2026 by Sinoquebec Medi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许可不得摘抄 | GMT-5, 2026-3-6 02:35 , Processed in 0.140356 second(s), 23 que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