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中国农历新年前夕,一场特殊的聚会在北京某高档酒店内举行。前来的是一群操着地道中国话的“老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普通的“中国通”,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洋孩子”。    聚会现场,一位叫柯马凯的外国人,带领大家唱起了《共产主义接班人》。  柯马凯:我们这个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是不是咱们唱一个《共产主义接班人》。 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1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英国。父亲柯鲁克和母亲伊莎白1947年来到中国,在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马凯兄弟三人从小就在“北外”的大院里长大。  柯马凯:我们这栋南楼,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第一栋公寓楼,那原来住的都是筒子楼,住的那种宿舍,这个里头有卫生间,有这个厨房什么的,整个就和现在的这个起居一样。大家早晨起来就是端着脸盆什么洗漱用具,跑到那儿排队,什么刷牙,什么什么洗脸什么的。早午晚三顿都是食堂,不花钱,没有钱,衣裳都是统一供给的,我们全都穿的一样。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流行,大批“左派”青年不满本国的政治制度,纷纷来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革命。他们中很多人从此留在这里。“1949年”后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和他们在中国出生的孩子,在马凯童年的记忆里,大人们一周上六天班,没人管的孩子们就聚在一起跳皮筋、弹玻璃球、“打仗攻城”、“抓特务”。    柯马凯:到周末,到这个没课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就跑到这个大教室里头玩一种游戏特别好玩。分两波,然后就是打仗,用那个皮筋套在手上,用纸屑叠一种小子弹,然后这么,这么一崩,我们的这不是有课桌吗,我们就藏了两拨。这头一拨,那头一拨然后互相打。那个时候爬了铁丝网就可以出去那边小河边儿,全都是庄稼地,我小时候也挺淘的,跑到那个玉米地里也掰过棒子,还有后来有一回还摘了些西红柿。我妈发现了以后,哎呀说我,说一定得去找那个社员去赔礼道歉,哎呀我当时觉得特别尴尬这事,还是去了。五岁以前马凯都不会说英文,虽然成长在异国他乡,但小时候的马凯却很少感觉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他身边有不少跟他一样的“洋孩子”。  2今年65岁的阳和平同样出生在中国,父亲阳早原是美国农民,1946年他卖掉了自家农场的三十头奶牛来到中国,阳和平和弟弟妹妹从小随父母在西安的农场里长大。     阳和平:农场的那个孩子们我是娃娃头,带他们玩那个捉迷藏,我们叫抓特务。几个人装成特务藏起来,然后大伙都追,哎呀玩得特痛快,我看到那个《地道战》电影,我们家旁边就原来有个自留地嘛,然后我在这挖一个坑,这挖一个坑,底下打通了,哎呀从这下去那钻出来好自豪,我爸爸下班回来一看,哎呀觉得不太对,麻烦了,我挨一顿揍。与在“北外”大院里的洋孩子不同,那时候整个西安都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阳和平从小就经常被嘲笑为“大鼻子”,为此他也没少和小伙伴们打架。   阳和平:我小的时候人家都说这个外国人长得真丑啊,他说他真替建平的妈妈伤心,说一个丑孩子还可以忍受,俩丑,好丑啊。对于自己的美国面孔,阳和平从小就感到自卑,阳和平从小就十分抵触父母教他英语。  阳和平:有一天我爸爸就检验我的英文学了多少,说这是什么,说nose(鼻子),这是什么ear(耳朵),这是什么,这是mouth(嘴巴),这是什么,my god(我的天)。哎呀他们大声笑,一下子把我这个笑得就是害羞,我好不容易学了一句英文还学错了,再不学这个东西了,就特别抵触。36岁时阳和平来到“北外”住了一年,他也因此和柯马凯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凯10岁那年暑假还去了趟西安,就住在阳和平家里。  实际上两家人的渊源由来以久。  马凯的父母在晋察冀边区做土改调查期间就曾与阳和平的父亲阳早和舅舅韩丁相识,韩丁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重庆谈判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并为其个人魅力所折服,之后便前往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8年在晋察冀边区小村庄十里店阳早为韩丁和柯鲁克夫妇拍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上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时候的他们不会想到在这片令他们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上,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伊莎白:当我第一次去十里店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就是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个坐的地方,人们就坐在门口吃饭。马凯的母亲伊莎白今年102岁,她在中国已经度过了近九十年的时光,1915年伊莎白出生于成都的一个加拿大传教士家庭。  父亲是传教士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也正是在这所校园里伊莎白认识了自己日后的爱人大卫·柯鲁克。  30年代,大卫·柯鲁克受左翼思潮影响,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大卫又加入了西班牙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负伤。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访问,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的《西行漫记》一经出版引发世界轰动,人们第一次知道在遥远的中国还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支队伍,西方许多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青年也因此纷纷来到中国“朝圣”。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正是这股红色大潮中的一员。   1938年大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成都他与23岁的伊莎白相识,并很快爱上了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加拿大女孩。   柯马凯:当时我父亲是共产党,我妈呢,没有什么政治信仰,但是我妈就是善良的那种基督教的那个慈善的那一套。我父亲爱上她以后,他们谈恋爱期间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暴力到底可不可行,我父亲终于说服了她,就说有些事你要是仅仅靠一个不采取暴力的话,受压迫、受欺凌什么的就解决不了问题。当年长征这个红军怎么怎么飞夺泸定桥,就讲这些故事。在大卫的影响下年轻的伊莎白也逐渐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1年伊莎白跟随大卫回英国参军投身反法西斯战争。  临行前两人还特意去了大卫无数次提起的泸定桥,并在那里订立婚约。  “二战”结束后,1947年已经完婚的夫妻俩回到伊莎白的“故乡”,他们发现中国的革命形势彻底改变了,胜利即将到来。  柯马凯:大势所趋,伟大的转折,中国胜利在望。那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嘛,他们非常兴奋,你想世界人口最大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国家,世界史上一个大事,打江山难,但是守江山,怎么怎么治理,这一个一个新的政权怎么这个经世济民,怎么发展,怎么建设,怎么构建一个新的社会。1948年应中共邀请,柯鲁克夫妇决定投身教育,为革命局势大好即将建国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阳和平的母亲寒春也放弃了在美国的大好前途奔赴中国。4寒春,美国核物理专家,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与杨振宁、李政道为同窗好友。   她曾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的“曼哈顿”计划,但不久看到自己参与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包扎后的惨状,年轻的寒春对自己从事的专业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阳和平:这个战争最教育人,战争也是最残酷的,它就非常明摆的,你不能说我要逃脱,你逃不开的,你必须有选择。我爸爸一直写信给她讲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这个中国的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说你什么时候研究核物理都可以,你现在不到中国来,你就错过末班车了,当然我也想你。1948年在当时还是“追求着”的阳早的感召下,寒春最终决定前往中国,第二年她与阳早在延安的窑洞里结了婚。   1952年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怀孕7个月的寒春作为美国人民代表参会,在会上她发言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阳和平:我妈跟着那个宋庆龄她们一块走出会议大厅,宋庆龄就问说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我妈说还没起呢,那就叫和平了。来到中国后寒春不再从事自己的核物理研究,而是与“卖了三十头奶牛来到中国”的丈夫阳早一起在延安养牛。  1949年后夫妻俩拒绝了去首都北京的邀请,依旧留在陕西养牛,过着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  5北京友谊宾馆始建于1953年,是由周恩来特别下令修建,用于招待在京的苏联专家。上世纪5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派驻大批专家来到中国援建,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来了一位苏联的校长助理。   柯马凯:我第一次进友谊宾馆就是苏联姑姑请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到门口还得登记,那个一个苏联专家谁谁谁,房号得说出来,然后还得打个电话确认,让他们进来吧,要不不让进。外国人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特别的防备。在“冷战”的大格局下,在华的“国际友人”也被分为了两大阵营,柯马凯的父母等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专家不仅工资仅有苏联专家的五分之一,在所在领域也逐渐失去了话语权,很多单位对苏联专家言听计从,加之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高涨,来自美国的专家和他们的孩子更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阳和平舅舅韩丁选择回了美国。     阳和平:我们就喊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然后我的同学就在我的面前,打倒美帝国主义,好像我是美帝国主义似的,总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总是抗美援朝,总是美国到处侵略扩张,总是负面的,总是觉得一个美国人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黑影,是一个不光彩的东西。阳和平从小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他时常困惑自己在中国生于斯长于斯,怎么就成了万恶的美帝呢。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离,此时马凯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好了父母父母的工资一下子翻了几翻,每月两人工资高达360块钱,他们也被获准自由进入友谊宾馆,享受这里的美食、游泳馆和电影院。每周马凯都骑车到友谊宾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聚会。   6然而这些洋孩子们眼中快乐、富足的生活在他们的父母看来却并不那么美好。196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对于像马凯的父母这些抱着共产主义信仰来到中国的欧美“左派”青年们来说,享受的高工资和福利正是他们最反对的特权化。   柯马凯:确实特权,你想我们五十年代同吃同住,到后来是分化了,你想想我父母那个时候还当时就觉得,工资太高了,还提出来说不能,我们就拿一半的工资吧,主动地挺革命,好像阳早、寒春他们也挺革命的,就觉得不能搞特权、特殊化。物质上待遇特殊,政治上却越来越排外,1963年中国开始四清运动,直接要求对外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内要做到内外有别。此时一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学习的阳早、寒春发现他们被边缘了。   阳和平:1964年、1965年开始农场搞四清运动不让他们参加,以前什么都参加,反右运动都参加,三反、五反都参加,运动不让参加,只能是做一个技术员,就等于是一个被雇佣的人,就是一个雇佣者了。那么在中国呆着干嘛。1966年在北京方面的极力邀请下,阳和平的父母最终极不情愿的离开了西安农场举家迁往北京,夫妻俩被安排在了相对轻松的译校工作,还给他们配了汽车,但两人坚决不坐,汽车只能在他们身边空驶,而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各处穿梭。    阳和平:他说服从组织分配,但有一条,北京的外国人都住在友谊宾馆,我坚决不住友谊宾馆,到了北京把他们安排在新侨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就没法沟通,他就不懂这俩人到中国来要是贪图享受根本不会到中国来的,结果把他们全放到金色的贫民窟,就是他们物质上是金的,非常高等的待遇,但是精神上那就是贫民窟里边。此时寒春、阳早并不知道几个月后一场风暴即将袭来,是机遇还是厄运,在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暴之中,这些金发碧眼的革命者是否会再次融入革命的洪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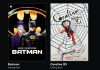




Copyright © 1999 - 2026 by Sinoquebec Medi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许可不得摘抄 | GMT-5, 2026-3-14 01:53 , Processed in 0.157611 second(s), 23 queries .